“雖然我的正式教學生涯已經進入倒計時,但是只要北大講堂的朋友們邀請我,大家仍然接受我,我就會一直站在這里。”2025年4月30日,北京大學百周年紀念講堂舉辦的“戴錦華教授電影導賞”系列第50場特別活動上,66歲的戴錦華懷抱學生們送給她的鮮花,滿臉笑意地給出了讓北大學子欣喜的回答,臺下近兩千名師生掌聲雷動。
作為北京大學最受歡迎的教師之一,戴錦華雖早已達到退休年齡,卻依然保持著高強度的工作節奏。她的日程表密密麻麻,除了完成每周的教學任務,還有各種講座、對談、學術邀請、電影節活動,以及國際旅行和訪問。每周三晚她在北大講堂的電影導賞,更是憑借三年不間斷的堅守,讓這場光影之約成為北大校園里極具影響力的文化名片,吸引許多師生與影迷慕名而來。
因將熱愛化作職業,戴錦華始終認為自己是幸運且幸福的。她說,自己一定會將工作堅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而這方講臺的存在,也意味著即便退休,她也會繼續活躍在這個被她自豪地稱為“世界最大的藝術影院”的地方,延續她與電影、與北大和學子們的難舍情緣。

1 墜入電影“愛河”
從北大求學到電影學院任教
1959年,戴錦華出生于北京。她的母親是一名小學語文老師,父親是文學愛好者,二人在她成長過程中留下了深遠的影響。自小學起,戴錦華便展現出極高的閱讀熱情,每年閱讀數百本課外書籍。學校圖書館的藏書很快被她讀完了,她只得四處尋覓圖書。借閱書籍練就了她快速閱讀的本領:一部20萬字以上的長篇小說,她五六小時便能完成通讀。
1978年,19歲的戴錦華以理科生身份叩開了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大門。彼時的她壓根兒不會想到,自己未來會成為中國電影研究、女性主義理論與文化研究的重要拓荒者。在那個百廢待興、“一切剛剛開始”的年代,北大自由包容的學術氛圍、濃厚嚴謹的治學環境,以及溫暖真摯的師生情誼,為她的學術生涯奠定了堅實的底色。
“那時剛剛恢復高考不久,我們那屆北大中文系,僅文學專業就有五十多人,年齡最長的37歲,最小的16歲,每個人的生命經驗千差萬別,幾乎很難歸為一代人。”戴錦華記得,當時許多德高望重的老師都在一線教學,“我最愛林庚先生講的《楚辭》課,記筆記寫到手指抽筋。”
她記得,很多老師剛剛重啟學術研究,對社會、對學生都充滿了熱望,會把自己最新的思考或研究成果立刻拿到課堂上分享;而學生們每有不同意見,就會在課堂上站起來反駁老師,甚至和老師唇槍舌劍。課后,有些老師還會到宿舍和學生繼續爭論。“當時的北大校園里,到處可以看見三五成群站在路邊爭論的學生,慷慨激昂、面紅耳赤。那是我生命真正的起點。”
1982年,戴錦華從北京大學畢業。出于對讀書和教學的熱愛,她選擇前往北京電影學院任教。“在那個充滿理想主義的年代,同學們大多懷揣著投身社會變革的熱忱,將報社、出版社作為職業首選,但我非常明確地想要去大學教書。”在她看來,成為一名教師并非沖動之舉,而是慎重思考后的決定,“選擇大學,不僅因為這里能讓我擁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時間,當時更渴望的是,畢生和青年共處,或許能讓我的心靈衰老得慢一些。”
初入北京電影學院時,戴錦華喜歡各種文藝形式,卻對電影“無知且無感”。在她眼中,電影充斥著商業氣息,顯得“媚俗”又“膚淺”,欠缺人文含量。“工作伊始,那于我而言只是一份教職,與電影藝術本身并無太多關聯。”
但命運的安排讓她的態度有了巨大轉變——初到電影學院的那個暑假,戴錦華因協助“第一屆全國高校電影課教師講習班”,獲得了一整套電影觀摩票。此后半年多時間里,她連續看了一百多部世界電影史上的經典之作,徹底改變了此前對電影的偏見。
《精疲力盡》《野草莓》《第七封印》《四百擊》《朱爾與吉姆》《奇遇》……當這些歐洲大師的影片在銀幕上展開時,她感到自己“陡然跌入了一場精神的、視覺的盛宴,陷入了一份不曾夢想到的狂喜或曰迷狂”。她形容那個刻骨銘心的瞬間,“我與電影共墜愛河!”
“看完《精疲力盡》,那種欲哭無淚、欲說無語的激動,讓我只想狂奔,對街上的每個人大喊:‘這是我的電影!我終于找到了我的電影’!”“我在這些影片里感到的是生命同頻、情感共振,我渴望表達的一切似乎都在這些電影里。”于是,她一往情深地愛上了電影,一邊教書,一邊自修電影攝影、錄音、美術系等專業課程,漸漸將思考和研究重心轉向了電影。
那時沒有多少中文電影研究著作,戴錦華只能泡在期刊室中,通過國外電影期刊,了解關于電影拍攝的細節和技術手段。一次她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看到一本英文專著,是法國電影理論家克里斯蒂安·麥茨的電影符號學開篇作《電影表意散論》英譯本。她借出此書,花巨款復印了全書,并且試著自己翻譯,逐字逐句啃下結構主義電影符號學的根基,由此進入歐美電影理論的世界。
中國電影資料館舉辦瑞典電影回顧展,她“一擲千金”,一氣兒買下了三套票,上午、下午、晚上各一場,全身心地沉浸在光影世界中。伯格曼的同一部片子她看了三遍,累得眼冒金星,“因為不知道下一次在哪里,如何還能再看到這些影片。”她在影院的黑暗中做筆記,常常感到挫敗、沮喪——回家翻開本子一看,字跡都重疊了,難以辨認。后來她收到國際同行贈送的一份特別禮物:一支自帶微光燈的圓珠筆,專門用于在影院做筆記。“我一直珍藏著一支,不舍得用,也不舍得扔,一直‘供’在書架上,久而久之,它最后都風化了。”
1987年,在時任北京電影學院院長沈嵩生的支持下,戴錦華與鐘大豐、李弈明共同創立了中國首個電影史論專業。從課程體系建設到教材編撰,她都親力親為,傾注了大量心血。“這個專業第一個班招生時,我跑遍了全國各考區,每一個都親自面試,選拔標準相當嚴苛。”作為這個班的主任教員、主講教員、班主任,她一人身兼三職,白天授課,晚上還要翻譯西方電影理論著作。“1987年到1990年,我送出了第一批電影理論班本科畢業生。”
在戴錦華看來,電影不僅是20世紀最偉大的藝術,也是洞見世界的重要窗口。她常對學生們說:“我們的生命,經由銀幕去和更廣闊的世界相遇,然后獲得一種反觀自己的能力。哪怕只有一次,哪怕只有一部電影,讓我們有了這樣一種感悟,那我們做這件事就值得,電影就值得。”

戴錦華教授導賞影片《倒倉》

每周三戴錦華都會出現在被她稱為“世界最大的藝術影院”的北大百周年紀念講堂
2 重返母校
以自身生命經驗開啟文化研究
在北京電影學院的11年,戴錦華實現了從文學研究者到電影學者的華麗轉身。1993年,時任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所長樂黛云邀請戴錦華回歸母校任教,開啟了她學術生涯的第二次轉型。
求學于北大的歲月里,戴錦華就和同學們一道,將樂黛云老師視為“校園偶像”。在課堂上聽樂老師神采飛揚地以尼采哲學視角解讀茅盾,趴在人頭攢動的辦公樓禮堂窗臺上聽樂老師講“西方新思潮”……這段經歷,不僅開啟了她的學術生涯,也讓她理解到為師者的意義和快樂。
樂老師的人格魅力和優雅風范對戴錦華影響至深。戴錦華回憶起自己首次應樂老師之邀參加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年會的情景。當時,她穿著短褲和T恤便到了會場,驚見被人群簇擁的樂老師一襲長裙,美麗端莊,意識到自己著裝不妥,趕緊出去買了裙裝再次出席盛會。
后來,戴錦華回到母校任教,樂老師為了引導戴錦華參與學院管理,特意把她喚到家中,悉心傳授“知人”與“用人”的區別。回想這一切,戴錦華無限感恩和慨嘆:“樂老師召喚和重塑了我對自己的希望與夢想,向我展示了一個教師的魅力、風采乃至一個學者的空間與可能性。她是我的偶像,是我生命的榜樣。”
在北大,戴錦華將目光從銀幕投向更廣闊的社會文化場域,從歐洲藝術電影到第三世界影像,從經典文本到流行文化。彼時的她,已不再滿足于對單一學科的研究:“當我嘗試用女性主義視角解讀電影,用電影研究的方法切入文化現象時,猛然發現學科壁壘只是人為的桎梏。”最早她只是憑著直覺,想把電影研究置于一個更宏大的參數和更廣闊的場域中去。“后來,我開始關注與研究文化市場,關注文化的生產過程,幸運地開啟了新領域的研究。”
在專注于文化研究的日子里,戴錦華與同窗孟悅合著的《浮出歷史地表》成為中國女性主義文學研究的里程碑。這本書通過解析廬隱、丁玲等女作家的文本,揭示女性在歷史敘事中的“隱形書寫”。但戴錦華拒絕將女性主義簡單地視為一種標簽,“對我而言,女性主義首先是生命經驗的自救。”
每次有人問她為什么變成了一個女性主義者,她都會實誠相告:“就是因為我長太高了,我十三歲就已經一米七五了,比很多男同學還要高。這讓我因為‘不像女人’而被審視,還總會聽到有人在背后竊竊私語說‘這樣怎么嫁人’。”她曾覺得自己在人生的意義上是一個有問題的女人,好在女性主義讓她明白,那些來自外界的規訓并非天經地義,一切并不是自己的錯。
在戴錦華看來,女性主義從來不是主義,也不是理論,而是一種實踐的人道主義。“它幫助我了解自己,了解世界,并且接受自己,相信自己。它是一個在我生命當中最有力量的支撐,同時也是一個我思考和觀察所有問題時最內在的角度。”
戴錦華的成長,還有一個非常具體的動力,就是她不想重蹈母親的人生軌跡。她的母親那一代人,一方面要和男同事一樣,在中國工業化進程最艱難的時代背景下投身勞動;另一方面回到家中還要承擔起照顧老小、相夫教子的重任,包攬所有家務勞動。她們強大的自我犧牲精神,促使其為社會和家庭無私奉獻了一切。
“我有時會特別強烈地感覺到,母親因為此前沒有發展出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在后來的歲月當中,無法安置自己。”正是通過母親這代女性,讓戴錦華意識到,“在雙重社會角色要求之下,我們要問自己,你要什么?什么使你快樂?什么使你幸福?什么是你不受他人要求,而是自己內心渴望的?我覺得這比什么都重要。”


3 擁抱互聯網
“云學生”超百萬
在北大,戴錦華的課堂是傳奇般的存在。她開設的通選課“影片精讀”被確定為全校核心課程,每次都爆滿。學生們為了能在教室里占有一席之地,常常提前兩小時便開始排隊等候。還有很多人跑來旁聽,窗臺、過道都擠滿了人。她的講授風格獨特:語速極快,長句如連珠炮,卻邏輯嚴密;拒絕“標準答案”,總能將復雜的理論拆解成一個個生動的案例。
她的課堂遠不止于電影,憑著跨學科的視野,她對泛文化領域的各類事件始終保持著強烈的好奇、熱忱,同時也不乏警醒與思索。在“文化研究”課上,她帶領學生們分析抖音、同人小說、AI孫燕姿翻唱……將流行文化置于資本、技術、性別交織的網絡中。這種“接地氣”的教學方式,讓學生驚呼:“原來學術可以如此鮮活!”
雖然熱愛教學,但戴錦華從教書的第一天開始,就一直反對“好為人師”。她說,“老師要千萬警惕自己成為學生的天花板,多求諸于己,而不是教化于人。”
戴錦華一直對精英主義持反思和批判態度:“精英主義容易滋生自戀。”在她看來,大學教育的核心價值在于強化老師對個體的關注。“比如我可以和學生面對面交流,這讓我有機會深入了解每一個人,然后和他們分享問題和愿望,盡可能幫助他們在學術之路上往前走。”她從不指定論文題目,而是鼓勵學生從自身困惑出發,自由選擇想研究的題目,然后陪伴他們一起思考,協助他們完成研究。“學術不是解題,而是與生命經驗的對話。”
2017年,“52倍人生——戴錦華大師電影課”上線,引起極大反響。2021年6月,戴錦華又以“戴錦華講電影”賬號入駐B站,首條視頻瞬間被“老師好”的彈幕刷屏。如今,這一賬號已收獲超過百萬粉絲,她也成為B站上最受歡迎的教授之一。她以縝密的邏輯、犀利的觀點與磅礴的語言,將電影批評、性別議題、文化研究等厚重內容轉化為“浪潮般的思想激蕩”,讓年輕觀眾直呼“醍醐灌頂”,許多人興奮地以“云學生”自居。
戴錦華坦言:“許多非北大課堂的聽眾積極反饋,對我而言是莫大的鼓舞。課堂內容進入社會各個空間,產生了與校園內截然不同的效應。”她欣喜地看到,這些知識引發了關乎個人生命與人生選擇的積極互動,這正是她一直以來在真實課堂中所期待的。通過網絡,她不斷與時代產生互動,“我沒有簡單地跟隨這個時代,而是在保持與時代對話。”
但她同時高度警惕網絡教學“知識簡化”的陷阱:“絕對不能因為媒介形式的改變而簡化思想,絕對不能做迎合與取悅大眾的任何預設。知識并不崇高,但是知識是嚴肅的,思想更是嚴肅的,我們得認真地去對待。我要讓他們真的感覺進入了北大的課堂。”
除了電影文化,戴錦華常常在網絡上回應人們關心的各種問題:年齡焦慮、親密關系、兩性話題——她從來都坦然面對,真誠應答,既有不落俗套的獨立視角,又總能把握好分寸尺度。人們在她這里得到的,不是簡單的答案,而是一種思考的態度。她說:“無論在課堂上,還是在互聯網上,面對任何聽眾,我都會呈現出最大的真誠。”

戴錦華與恩師樂黛云(左)
4 直面衰老與死亡
帶著內心的幼稚與赤誠
教學生涯只是戴錦華生命的一個面向,她更引以為傲的是自身生命的多元與豐盈。十余年來,她投身中國鄉村調查與新鄉村建設運動,與經濟學家、社會學家、農學家一同深入貧困山區,貼近特困群體。她參加鄉村婦女的讀書小組,給她們做演講,暢談大眾文化、傳媒娛樂,剖析農村發展困境。“她們好喜歡聽,出去就能一字不漏地復述,從來沒有覺得聽不懂我說話,反倒是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說聽不懂,這很好玩。”
2000年之后的十年間,她還與一些做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朋友,共同開啟了第三世界考察之旅,足跡遍布印度、泰國、巴西、委內瑞拉等數十個國家,進入深山、叢林、鄉村、營地,見過不同的基層組織、民眾團體,甚至游擊隊。戴錦華最關心的,永遠是底層人的社會境況和文化思想。“當我們乘越野吉普穿過拉美,親身去感知這片土地時,我才知道當年觸動切·格瓦拉踏上征途的問題,至今仍未得到改善。”
在對第三世界研究的過程中,戴錦華從拉美的反抗者那里學到了她自認為最寶貴的一課——拒絕悲情。戴錦華闡釋道:“拒絕悲情,首先就是歷數迫害者、壓迫者的不義并不能使你自己的正義不言自明。你要去思考你的正義,要明確地大聲說出你要什么,而且試圖去獲得和抵達自己渴望的目標。另外一個層次就是,不讓敵手的不義變成傷害自己、摧毀自己的力量;相反,要盡可能把他們的傷害從自己的身體里移出去,不讓自己攜帶著它,而是保持一個飽滿、快樂的生命狀態。”
當戴錦華“行萬里路”后,再度回歸電影研究時,她突然發現自己有了完全不一樣的視野。“以前我看不到它背后的歷史文化和真實的人,而這樣多研究領域的涉入,讓我在一個新的場域接受新的挑戰,打開自己,然后舊的場域也變成了新的世界。這真的是一個非常快樂的過程。”
戴錦華邊行走,邊記錄,她的微信朋友圈成為她日常攝影的圖片展:未名湖面的水禽漣漪,暮春初夏的姹紫嫣紅,課間偶遇的銀杏驟雨,校舍古建的飛檐落雪,還有異鄉街頭歷史刻痕的凝望瞬間。這些畫面極具大師的電影質感,引得朋友們紛紛點贊收藏,并攛掇她將攝影作品結集出版。
在同齡人多已退休、安享晚年的年紀,戴錦華像她的偶像切·格瓦拉一樣,還在不停前行。“我始終享有年輕時初涉電影學時的那份快樂,一直在不斷打開一些新的場域,世界在我腳下。”
2022年12月25日,戴錦華的母親離世,她不得不直面死亡與衰老這一命題。“33年前,我父親去世后,我就一直陪伴著母親。當她也離我而去時,我才意識到,一旦脫離了這種愛的羈絆,自己就要在創痛之后經歷一個重新定義自己、安置自己的過程。”
母親離世也迫使戴錦華正視自己老了,但她并不恐懼:“自然生命的進程不可避免,但在精神層面,我仍為自己的年輕與幼稚感到驕傲。只要還能發問、追問,在探尋答案中收獲快樂,就不算老去。”
“我無法達到在現實世界中游刃有余、進退自如的那種成熟,”而且她也不愿如此,“我想保持我的幼稚,承認我的無知,就這樣走下去,直到死亡降臨。”
來源:北京日報 王潤
流程編輯:U022
如遇作品內容、版權等問題,請在相關文章刊發之日起30日內與本網聯系。版權侵權聯系電話:010-852023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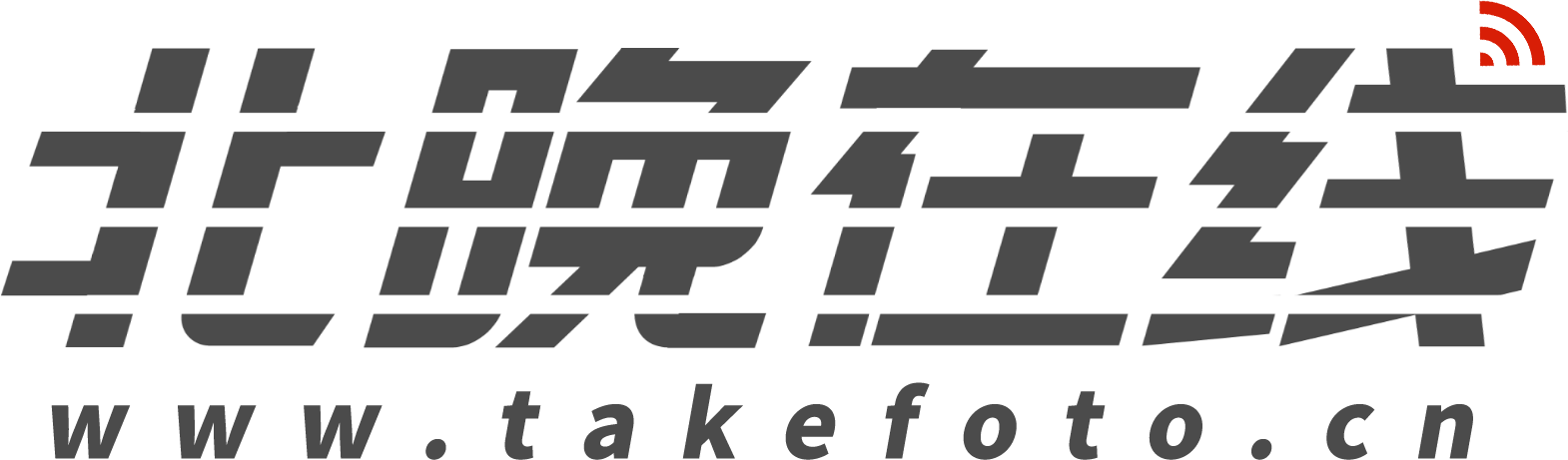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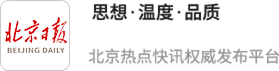





















未登錄
全部評論
0條